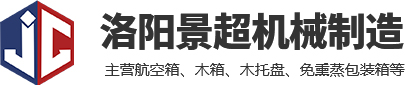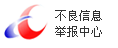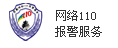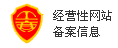表面上看,土地流拍只是影響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,實際影響的卻是社會融資。一旦社融斷崖式下降,政府又失去作為最后借款人的能力,就會觸發銀行系統性風險。
如果真的要“房住不炒”,土地就根本不應該以招拍掛的方式出讓(包括“集中出讓”)。因為只要土地是以“炒”(招拍掛)的方式定價的,住房就一定是“炒”的。
房地產在中國經濟中的基礎作用,使其相關政策在中國經濟中具有任何其它政策所不具有的宏觀影響。一步走錯,就有可能帶來遠超1989年“價格闖關”的災難性后果。
據《中國房地產報》報道,9月以來,相繼有長春、福州、天津、青島、濟南、成都、蘇州、沈陽等多個城市在第二輪集中土地拍賣前臨時暫停出讓。沈陽累計有24宗地塊在開拍前一天停牌,占第二批集中供地總量的52%;濟南有20宗停牌;天津19宗。流拍率也步步走高:沈陽、長春、福州、濟南和天津等城二輪土地出讓流拍率均超30%,廣州實際流拍率超過78%,杭州競品質地塊更是全部流拍。
01大面積流拍原因
此次大流拍涉及的城市從南到北,覆蓋幾乎全國所有主要城市,表明流拍原因并不是地區性和偶然性的,在我看來,它是之前全國一系列房地產政策的組合結果。過去幾年,從棚改開始的城市更新吸引了大批民間資本。為了完成GDP指標,各地政府假開發商之手借錢大拆大建。特別是發端于沿海發達地區的“房地產+三舊”的更新模式,向原本進入不了土地一級市場的開發商敞開了大門,“土地整備”演變為開發商和原住民的饕餮。雖然中央最近發文制止了大拆大改模式的蔓延,但前一階段通過“三舊”改造已經形成的新增商品房開始對市場形成巨大供應壓力。
疫情產生時,經濟遭受空前打擊。國家層面鼓勵地方政府依托平臺公司發債,平臺公司資金充裕。商品房的本質就是資本市場,其價格不是反映住房的供需關系,而是資本價格的投影。為了應對大流行放松銀根的結果,必然反映在資本價格上。在美國是股市,在中國則是房市。2020年中,地價、房價瘋漲,就是央行寬松貨幣的必然反映。住房價格的上升,直接引發了政府對房地產價格空前的各種“限價”、“限售”。針對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的各種交易限制,對地方政府問責,使房地產相關資產的流動性幾乎完全喪失。
特別是“三道紅線”的判斷標準逐漸成為常規金融機構的底層要求。行業企業陷入不拿地馬上死,拿了地很快死的惡性循環。金融機構放貸嚴控,包括開發貸和按揭貸。非銀行融資成本進一步提升,境外融資市場成本同步提高。加上從2021年初起,原材料漲價進一步提高了地產開發成本。至此,大多數民營房地產企業都陷入流動性危機。到7月份開始,大量地產企業出現信用違約,企業不得不拋售資產套現。而各地為了社會穩定和金融抵押品安全,限制開發商低價銷售。最后,“集中供地”抑制了通過連續拿地接續流動性的“快周轉”融資模式。地方政府與開發商從原本“一對多”賣方市場變為“多對一”買方市場。10月份開始的第二批最終導致了當前土地大面積流拍。
02資產負債表危機
土地流拍的最大危險,不在于地方政府突然“沒錢了”,不在于開發商的樓“爛尾了”,也不在于房地產產業鏈上無數的就業瞬間消失了,而在于中國過去高速成長賴以的基礎——信貸以及與其密切相關的貨幣生成——突然消失了。果真如此,土地流拍導致的就不是周期性經濟“下滑”,而是中國經濟大歷史曲線的“脆斷”。
最近經濟學家辜朝明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。他認為以前“央行是最后的貸款人,但我們現在不再需要了”,在信用貨幣時代,在貨幣供大于求的條件下,“我們需要的是最后借款人……政府借款實際上比央行更重要”。在美國,資本的來源是國債,美元是本幣,匯率是浮動的,國債等于直接融資;而在中國,貨幣與美元掛鉤,人民幣是美元的延申,國債不是直接融資。
中國貨幣的自主性,實際是源于M2生成機制。在生成M2的社融中,房地產占據最大的份額。而房地產的“根”——土地資本——的創造,靠的就是地方政府借款。地方政府最主要的抵押品和信用,都是直接或間接來自土地。房地產在中國資本市場上的角色,遠比其他任何國家都重要。
如果土地大規模流拍,土地為核心的資產就會貶值。表面上看,土地流拍只是影響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,實際影響的卻是社會融資,而后者乃是現代貨幣生成的關鍵一環。一旦社會融資斷崖式下降,政府又失去作為最后借款人的能力,就會觸發銀行系統性風險。無論1998年“房改”還是2008年“四萬億”,背后支持中國經濟脫離全球經濟曲線的,都是房地產。今天,在中美貿易摩擦的關鍵時刻,中國手中最大的牌,依然是房地產。沒有土地金融力量的支持,從抗疫到應對中美貿易摩擦,從農村振興到發展高科技一系列經濟目標都會成為空話。這才是當下土地流拍更深層的危險。
這樣的擔憂并非杞人憂天。房地產調控政策趨嚴之下,居民房貸需求繼續受到抑制。9月份,30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積較8月繼續回落,同比跌幅擴大至-33.4%。根據10月13日,央行公布9月份金融數據,9月居民中長期貸款增加4667億元,同比少增1695億元,減幅較上月進一步擴大(-1312億元)。資產負債表衰退的巨大陰影已經浮現在中國經濟的地平線上。
8·23信貸形勢分析會后,銀行加大了信貸投放。9月29日,人民銀行、銀保監會聯合召開房地產金融工作座談會,提出金融機構要配合相關部門和地方政府,根據城市實際需求,因城施策,合理安排房地產信貸投放節奏,避免信貸大面積收緊誤傷剛需基本住房需求。“大流拍”中首當其沖的受害者地方政府也開始自救。繼多城市政府先后發出限跌令后,10月9日,哈爾濱市一口氣發布多條利好購房者和樓市的新舉措,被一些媒體稱為“打響了救市第一槍”。10月15日下午,中國房協召集10家重點房企開會:聽取意見與建議,維護行業穩定——表明監管方面意識到了房地產被過度抑制后的負面后果。央行很清楚,只要貨幣需求萎縮,即使貨幣政策再寬松也無濟于事。
03資本市場還是商品市場?
只有找準問題出現的原因,才能對癥施治。土地流拍背后深層原因,在于我們對房地產市場的本質缺少深刻的理解。住房問題之所以復雜,在于其既有資本品的功能,又具有普通商品的屬性;既要完成融資的要求,又要解決住的問題。而這兩者的政策目標在很多時候是相互沖突的。作為資本品,其價格越高,創造的資本就越多,勞動力越便宜;作為商品,其價格越高,居住成本就越高,勞動力就越貴。
這種既要“炒”,又要“住”的特點,使得我們的房地產政策總是左右搖擺,首鼠兩端。每一輪成功打壓房價之后,必然緊接著又要防止房價下跌。房價漲,政府愁;房價跌,政府也愁。一腳油門,一腳剎車,市場有時候會無所適從。要真正建立起房地產市場的“長效機制”,唯一的辦法,就是通過制度設計,將住房的資本品和商品兩種屬性分開,在不同的市場分別定價。道理很簡單,你不能用一個房子實現兩個矛盾的目標。
如果我們想投資一個汽車企業,我們就到資本市場去買這個企業的股票;如果我們想買汽車,我們就到商品市場上購買汽車。汽車降價或漲價不影響其股票的上升與下跌,兩個市場是分開的。但住房市場不一樣,由于房地產的資本屬性沒有證券化,如果你要投資一個城市,你就必須購買實物住宅(盡管你并沒有居住需求)。如果你要自己居住,你也只能從資本市場進入,購買資本市場標價的住宅。這就好比你只能通過購買汽車股票獲得汽車。
如果你給同一個住宅的兩種需求標定不同價格,就會有人從這兩個市場套利。1998年房改一開始商品房和經濟適用房是分開的。甚至最初設想房地產市場是以經濟適用房為主,商品房作為補充。但隨著商品房價格迅速上升,和經濟適用房價格之間出現巨大落差,瘋狂的套利迫使雙軌制的住房體系必須并軌。由于地方政府必須依賴土地融資完成城市化的重資產(七通一平、電力電訊、學校醫療等),土地融資的巨大需求決定政府最終選擇了犧牲掉住房的商品屬性。
資本市場的價格,反映的是資產未來收益的估值;商品市場的價格,更多是反映商品生產的成本。在不少人看來,房價上升是“炒”,房價下跌不是“炒”。打壓房價,就是打壓“炒房”。殊不知,只要土地是通過拍賣進入市場,住房價格就必然是資本品的價格,此時無論政策是抬升還是打壓房價,本質上都是變相的“炒”。如果真的要“房住不炒”,土地就根本不應該以招拍掛的方式出讓(包括“集中出讓”)。因為只要土地是以“炒”(招拍掛)的方式定價,住房就一定是“炒”的。
顯然,房地產對于中國資本市場的巨大作用,使得中國經濟已經回不到沒有房地產的時代。教條地理解“房住不炒”的最終結果,必然是房地產資本市場的崩盤。一旦巨額的資本形態的財富一夜消失,我們立刻就會回到和印度一樣的低資本發展中國家。今天的房地產已經深度嵌入中國經濟。你可以說房地產綁架了中國經濟,反過來也意味著沒有房地產,也就沒有中國今天的經濟奇跡。
正確的“房住不炒”不是去除住房的資本功能,而是要把住房的資本屬性和商品屬性分離。只有這樣,才能把“油門”和“剎車”分成兩個腳踏板,資本與商品各自滿足不同的市場需求。有區別才能有政策。屬性分離使得我們可以針對“住”和“炒”兩個市場制定有區分的政策。現在的房地產市場,本質上就是一個資本市場。積累了從政府、企業到家庭巨大的資本性財富,是經濟目前最主要的信用來源。因此,各部門出臺的政策首先都必須立足于“保”。保不是要維持不變,而是要根據資本品供給過剩的現實“限量保價”。
針對已經進入市場的土地和在售住房,要協助企業有序出清,不能毫無預警抽貸。不動產市場交易的核心功能,就是給處于非交易狀態的資產定價。只要房價不出現暴跌,社會存量資產的價值就不會貶值,就不會出現系統系風險;同時取消各種限貸、限購、限價的政策,要將保障房地產市場的流動性而不是房價作為首要的政策目標。保證政府、開發商、銀行、散戶的有效履行其契約,特別是不得隨意抽貸、凍結資產。
針對未進入市場的土地,包括通過工改居、村改居、棚戶增容等渠道進入商品房市場,則要大幅度壓縮。“不炒”要從賣地這個源頭開始,而不能從開發商賣房開始。要引導現有房地產企業從開發商向運營商(從新建向運維服務)有序轉型。有序分流整個產業鏈的就業。新的住宅供地要從招拍掛市場(“炒”的市場),轉移到保障房市場(“住”的市場)。只有改變供地模式,才能真正做到“房住不炒”。
如果說“炒”的市場是“限量保價”,那么“住”的市場則相反要“限價保量”。所謂“住”的市場,指的是以成本為基準的保障性住房。這一市場與資本定價的市場要有嚴格區隔。需要指出的是,“住”的市場不能簡單理解為“租”的市場,“租”固然可以與“炒”的市場加以切割,但并沒有解決“住房問題”。現在那些無房戶就是靠租房。所謂“保障性租賃房”是在解決市場已經解決了的問題。市場上并不缺少“租”的住房。真正的“住房問題”不是無房可租,而是無法負擔自有住房。實踐中,計劃經濟時代留下的“公房”至今仍是政府難以解決的難題。在脫離資本市場的計劃經濟時代,保障性住房的投資根本沒有來源。
正確的做法是,只要城市有貢獻的(“五險一金”、個稅等)無房戶都可以以“先租后售”或“共有產權”等居民負擔得起的方式,低價格獲得自有住房。“先租后售”是居民以租賃方式獲得住房期權,滿足一定年限后解禁期權,租金轉為按揭。條件是解禁期要足夠長才不會沖擊商品房市場。共有產權是政府與個人共同投資商品房,在交易環節政府和個人分享土地升值。條件是確保購房者為無房戶,否則很容易將現在有錢人炒房變為政府與散戶共同炒房。
由于這兩種方式的保障房都可以進入資本市場,因此可以成為有效的抵押品。特別是“先租后售”由于抵押品風險極低,可以通過銀行大規模融資,從而起到彌補房地產市場供地減少導致的社會融資缺口。只要規模足夠大,與資本市場掛鉤的保障房一樣可以釋放出大量廣義貨幣,起到對沖社會融資下跌,保障市場流動性充足穩定的宏觀效果。在雙軌制的住房長效機制里,商品房市場價格高,就不再是“壞事”。由于作為抵押品保障房在資本市場具有較高的估值,保障房融資的成本就可以更低,而較低的財務成本可以支持更低的保障房價格和更大的建設規模。解禁期到期后家庭從住房獲得的財產性收入也就更大。
04辯證理解“房住不炒”
今天的中國已經成功建立起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住房市場。任何簡單的打壓都會帶來巨大的經濟危機和難以預料的社會動蕩。在激烈的大國博弈環境下,錯誤的房地產政策尤其危險。中國房地產政策反復多次的“收放循環”(包括這一次),已經證明目前只有“炒”沒有“住”的住房制度已經難以為繼。新的住房政策必須走向“房住不炒”這是毫無疑問的,但前提是要正確理解什么是“房住不炒”。
這一輪新的房地產治亂周期,一個根本原因,就在于各部門教條主義地理解“房住不炒”。看上去,每一個部門出臺的政策都是“合理”的,都在落實“房住不炒”,但其合成的效果,則是和“房住不炒”預期的宏觀經濟目標往往背道而馳。這就好比打贏了戰役,但從戰略上看最后沒有打好整個戰爭。土地流拍只有放到全局,才能理解為什么每個都“正確”的政策,卻導致了最終的合成謬誤。
“房住不炒”原則一定要放到它當初提出的大背景里才能正確理解。這個背景是住房市場“炒”的屬性已經充分發揮,但“住”的屬性幾乎是空白。因此,這一政策針對的增量而不是存量,目的不是“打壓房價”讓老百姓已經擁有的資產縮水,也不是“只租不售”和老百姓爭奪租賃市場,而是要幫助新市民無需通過“炒”(基于資本估值)的市場就可以以“住”(基于建設成本)的價格獲得居住權。要建立基于成本的房價體系,首先要解決的就是資金的來源。而只要將保障房與資本市場掛鉤,保障房就可以將自身變為有效的抵押品。在這個意義上,打擊房地產(“炒”)也是在打擊保障房(“住”)。
可持續的房地產應該有資本市場和保障市場“兩條腿”。現在資本(“炒”)這條腿異常強大,保障(“住”)這條腿卻還非常短小。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加長“住”這個短腿,而不是鋸掉“炒”這個長腿。“住”是目標,“炒”是工具。只有借助“炒”這個工具,才能解決“住”的問題。缺少任何一條腿的房地產都是不完整的。
只有辯證理解“房住不炒”才能正確處理“住”與“炒”的關系,才能設計出一個“住”與“炒”分離的住房制度,才能從根本上徹底解決反復出現的“住”“炒”循環。房地產在中國經濟中的基礎作用,使其相關政策在中國經濟中具有任何其它政策所不具有的宏觀影響。一步走錯,就有可能帶來遠超1989年“價格闖關”的災難性的后果。房地產既可以成就中國經濟史詩般的崛起,也可以導致中國經濟的停滯甚至危機。“載舟覆舟,所宜深慎”。
(文/廈門大學教授趙燕菁)